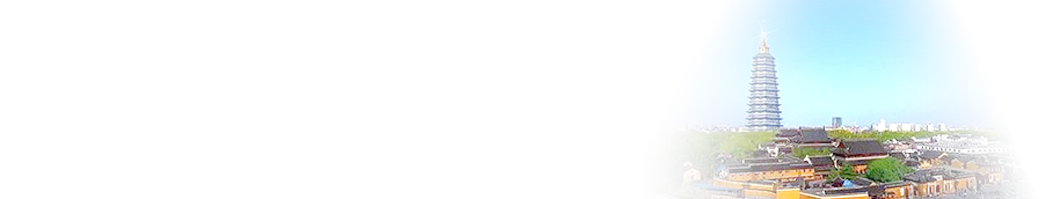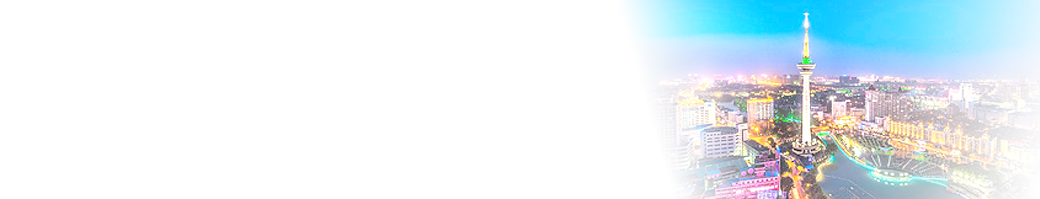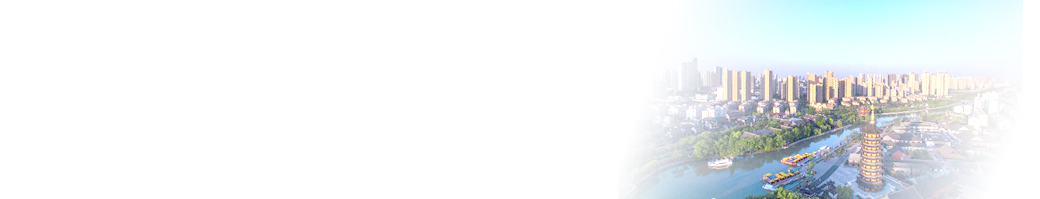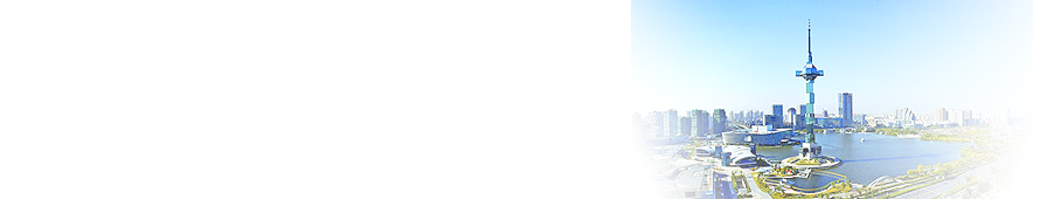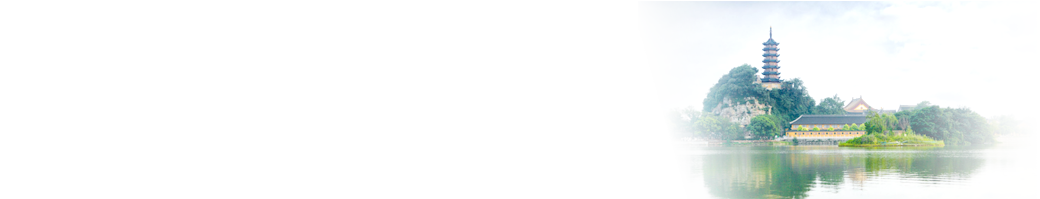雷墨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残酷的方式再次证明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之间的联系。致命病毒引发的神秘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再次超出人类的想象。
目前普遍认为,虽然“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不如“非典”病毒,但传染性却远超后者。这极大地增加了防控的难度,同时也凸显了国际协调的重要性。不过,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致命病毒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危险,与现实的防控措施和能力之间,都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危机四伏
人类肉眼不可见的致命病毒,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2019年9月,也就是本次疫情暴发3个多月前,一个名为“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的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危机四伏的世界: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工作年度报告》的文件。这个成立于2018年5月的国际组织,由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召集,主要任务是追踪世界范围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评估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对这类事件的措施和能力,并就此提出政策建议。
在普通民众的印象中,神秘病毒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有2003年的“非典”,还有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出现于西非而且近年来多次暴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禽流感”“猪流感”寨卡病毒等。但病毒肆虐的真实状况,远比人们感受到的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1年至2018年间,世界范围内有172个国家出现了1482起病毒引发的传染病流行事件。
上述文件基于世卫组织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报告得出结论:过去数十年,传染病暴发呈逐年上升趋势,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日渐增大。“如果过去只是序幕,那么一个真实存在的威胁是,快速传播的高致命性呼吸道病原体大流行,将夺取5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令世界经济的近5%化为乌有。如此大规模的全球传染病大流行将是灾难性的,会造成大范围的混乱、不稳定和不安全。世界将猝不及防。”
1918年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之后,人类社会再没有出现过因传染病流行而导致的千万级人口死亡的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悲剧不会再次出现。美国的“疾病建模研究所”通过大数据技术预测病毒传播后认为,如果现在出现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的高致命性呼吸道病原体大流行,将在6个月内导致全球3300万人死亡。《时代》杂志2017年5月的一期封面报道写道,世界并未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准备,出于种种原因,人类比100年前更加脆弱。
更加脆弱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缩小了其与带病毒动物之间的物理距离。截至目前的科学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恶性传染病都是因为病毒在野生动物体内“跨界传播”到人类。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人类流动性增加,越来越膨胀的人口千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以及几天内就能让人们从地球的偏远角落抵达地球任何地方的便捷交通,客观上都在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也就是说,与100年前相比,病毒与人类的距离更近了,其传播“效率”更高了。
某种程度上说,人类脆弱的根本原因在于病毒的“未知”特性。数百上千年前,瘟疫大流行被解释为“天神发怒”,逻辑是对“未知”的恐惧。进入现代科技时代,虽然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大幅降低,但人类应对病毒的能力还远谈不上、事实上很可能也做不到胸有成竹。人类科技发展的同时,病毒也在不断进化,这是病毒学领域的一个常识。在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非典”病毒的近亲。
从科技角度来看,人类与病毒的较量中,相对于100多年前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通过基因技术快速地“捕捉”到导致传染病的病毒、追踪到病毒的原始宿主和传播路径。但是,病毒如何进化以及是否会进化到更具传染性、更加致命的程度,“决定权”不在人类,而人类打造出“对称武器”——疫苗或药物,需要时间。换句话说,人类与致命病毒的较量,没有完成时,永远都是进行时,而且人类永远都处于被动的地位。
应对不足
“人类改变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脆弱性。”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1976年撰写的《瘟疫与人》中,梳理了过去几千年人类遭瘟疫侵袭的历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那时的基因技术方兴未艾,现代医学也未发展到如今的先进程度。不过,40多年后,麦克尼尔的悲观结论依然站得住脚。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人类与致命病毒较量的过程中,科技一直冲在最前沿,但政府政策行为向来都是短板。
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很长,但这种斗争真正上升到政府政策层面,却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标志性的事件是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对抗霍乱、天花的大流行。而对抗传染病流行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始于1946年世卫组织的成立。1951年,世卫组织通过《国际卫生条例》,要求成员国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并采取措施防止疫情蔓延。但“条例”的执行效果并不好,防疫基本上是国家内部事务,事实上没有形成国际协调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转折期,触发因素是艾滋病的扩散。当时,艾滋病在美国演变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美国政府开始加大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投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世卫组织多次修改《国际卫生条例》,在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穷国家医疗援助的同时,也鼓励在防控传染病上开展更多的政府间合作。20世纪末,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传染病所造成的危险,是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
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另一个转折点。美国公共卫生问题专家劳里·加勒特,在其2006年撰写的《逼近的瘟疫》中写道,“非典”疫情预示着一个新时期——全球流行病时期的到来。她的主要依据是,与此前的传染病流行不同的是,“非典”疫情代表着神秘未知病毒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世界”。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非典”疫情最终蔓延到30多个国家,导致8000多人感染、近800人死亡。
2005年,世卫组织再次修改“条例”,196个成员国承诺把“未知威胁”纳入国际防控合作范围。但是,做出承诺与兑现承诺之间的距离依然很长。有的国家出于种种考虑,连最基本的疫情报告义务,执行得也不尽如人意。比如,2007年印尼暴发H5N1疫情后,就曾拒绝与外界分享病毒样本。世卫组织2012年的报告显示,成员国中只有15%的国家达到了“条例”要求的标准。重要的原因在于,世卫组织被赋予的权力并没有“牙齿”,它更不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的“安理会”。
既然人类永远处于被动,那么就应更加注重防控。但就目前来看,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严重的“能力赤字”。2019年10月,来自2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了一份题为《全球健康安全指数》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通过预防、疾病监测和报告、快速反应、医疗系统、国际规则承诺、环境危险度等6个类别,以及34个具体指标,评估了195个国家预防、发现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在这项总分为100的评估中,得分66.7分以上被认定为具有较强的危机应对能力。195个国家的平均得分是40.2分,也就是说,整体上世界并不具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这些国家中,只有19%的国家达标。得分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83.5分)、英国(77.9分)、荷兰(75.6分)、澳大利亚(75.5分)、加拿大(75.3分)。亚洲国家中排名最高的是泰国(73.2分,世界排名第六),中国的得分是48.2分(世界排名第51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的“医疗系统”这一项得分普遍不高,平均得分在6个类别中最低(26.4分)。即使是总分最高的美国,“医疗系统”得分在6个类别中也是最低的(73.8分)。基于此,那份报告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为重大传染病的暴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代》杂志那个封面报道援引疾控专家的话称,传染病大暴发不像其他自然灾害那样限于单个区域,一旦暴发,再好的医院也会快速耗尽床位和医疗呼吸器。
政治病毒
病毒引发的传染病流行,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在政策和投入上的不足,造成了危机应对能力赤字。这些状况再加上“政治病毒”,那么对于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2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中提到,要警惕妨碍中美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政治病毒”。他在谈及本次疫情时说:“可能有些人试图利用当前的形势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甚至推动两国人民‘脱钩’。”
崔天凯大使谈的是中美关系中的问题,但却隐晦地点到了目前美国政治中不利于应对全球健康挑战的“病毒”。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近期公开表示,中国的疫情有助于美国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回归美国,有助于美国制造业的振兴。作为美国政府高官,罗斯这样的表态,在政治道德上令人侧目。但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政治道德的评判上,可能并不会让国际社会给出高分。
1月29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今日美国报》上撰文,称特朗普是最不适合带领美国应对全球健康挑战的领导人。他认为,传染病不会止步于国界,建墙无法阻挡疾病流行。“如果不帮助别人获得安全,我们自身也无法确保安全,也无法获得他国帮助带来的好处。”
2014年初,在奥巴马政府的力推下,数十个国家启动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在疫情防控、病毒监测和协调应对上加强合作。该项目成立后不久,就在应对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项目的最大出资国,虽然奥巴马政府向他国提供医疗援助有拒病毒于国门之外的考虑,但很难否认其中积极的政治道德因素。
而特朗普在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就把这个项目的预算削减了2/3(从1.8亿美元降为6000万美元)。这里面,毫无疑问也有政治道德因素。就全球健康面临的挑战来说,“美国优先”转化为“政治病毒”,或许比人们想象的容易。